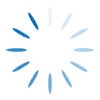“记忆是选择性记录的,个人记忆长时间不融入集体记忆被遗忘也是正常的。我们对你的头部经过检查后发现,的确和您想得一样,在经历过重大意外后某些让你感到疼痛的碎片化物象发生了细微的偏差。”
“比如旧记忆覆盖了部分新记忆,就像您说的能记得一些事但想不起来具体是谁,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我们觉得没有刻意治疗的必要。而且你心里其实也有答案,知道那部分的针对目标是谁,没必要对自己的情感空间太过严苛啦。”
“就像《秋园》写的那样,我建议您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把你想到了零星散乱的回忆都提笔写下来,方便很多故事相互串联起来,用笔赶路,把你想走的那段路重新走一遍就行了。”
医生想了想,继续说道:“据你所说,那段回忆与您爱人有关是吗?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或许在经历爆炸事故时您就像恶龙保护自己的宝石那样,第一时间就想把你最喜欢的东西藏起来,然而适得其反,越小心翼翼越容易出问题。”
“这比喻确实不太恰当。”
医生听完林付星的话也腼腆地笑了下,“总不能真对脑部进行电击治疗什么的吧,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啊。”
“听您安排了医生。”
“都是小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记忆缺失,而是你以前经历过非常极端的厌恶疗法,这种治疗的后遗症相信你也切身感受到了,就像你说的……在与伴侣发生性行为时会触发心理抵触甚至身体会有抽搐、干呕、耳鸣等情况,我对你经历的事感到心疼,希望在之后的治疗里您能积极配合,也能按时吃药。”
“放心吧医生,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林付星有些好笑地想,记忆缺失也比什么厌恶治疗让她头疼多了。
早年她还庆幸林德功给她找的那医生被逼她喝符水,因为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被驯化了叁天叁夜,出来后手上密密麻麻的针孔,出国后也不是没有治疗过,但吃什么药都反胃,还因为药物胖了几斤。
大概因为那段时间她太应激,急于出效果,反而总是出问题,现在丢了工作,没以前忙了,阅历也上来了,反而比以前好治疗了。
这次能彻彻底底出院了吧。林付星想。
“你聊到‘不影响正常生活’,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林付星手指交叉着,像是接下的话有些难以启齿似的,和医生聊性生活都能面不改色,聊到这个却仿佛有些不知所措。
“为了自己活着有紧迫感,我曾为自己制定了‘23岁是世界末日’的计划。这个想法其实挺幼稚的,但我为了这个目标,期间学了很多技能本领,乐此不疲,也在18岁之前已经能老练地很成年人打交道了,用现在流行的词……说话很油腻?那时候很多同龄人都说我比较早熟,或许是因为我太早和钱打交道了吧。”
医生听了她的用词笑了下,不置可否。
“然后?”
“我虽然在治疗腿伤期间想过一了百了,但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催我‘快来站起来啦,你得回国啦’‘回国很重要啦,还有很重要的事在等你解决啦’什么的,我之前怎么没发现自己这么爱国,又或许是我的事业粉给我托梦吧。”林付星打趣道。
她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这才开始说重点。
“回国后,我发现有人在我背后一直在搞小动作,虽然做了很多破事,但也经常帮我收拾烂摊子,我突然有一种摆烂的想法,如果我搞砸了,事情会怎么样?我做事不再瞻前顾后,甚至可以称得上为非作歹,经常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简直跟18岁完美主义的自己判若两人。”
“所以无论是是失去记忆还是经历的伤痛,让我缺少了些成年人该有的行为处事,又或许和我的工作环境有关吧,搞得我现在像个巨婴一样。”林付星自嘲道。
医生听完心中叹了口气,还是决定再给她加点剂量,不过最后她还是贴心地补充道:“据我所知,您在事业上已经比同行好太多啦,起码在赚钱上,您的脑子是绝对没问题的,行为处事也是因人而异……而您刚刚说的那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有人给了你某种信号,你接受到了这个信号,让你产生了自身很反感但又作死地还想继续的行为。”
“通俗来讲,你是在行驶被爱的权利。”
林付星倏然抬起头,医生当着她的面,好心地帮她点破了她不明白的问题所在。
“那我们可以正式进行治疗了?”
“......可以的。”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