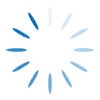守在一旁的几个男人早就憋不住了,佐敏吞话音未落,他们便像饿狼似的扑向瘫软在地上的女孩。刚被撕裂的下体还针扎似的疼,看着向自己一步步逼近的野兽,她哭着求饶。
但带着恐惧的颤音只换来几人更兴奋地淫笑,他们边走边解裤带。女孩见状,无暇顾及被撕碎的衣服,她双手撑着地板,试图站起逃跑,却因腿软而摔到在地。两只被绳子捆着的手,早已泛红发紫,麻绳陷进娇嫩的皮肤中。她忍着疼,手脚并用,跌跌撞撞爬向门口。每爬一步,身体都控制不住地发抖。
男人们不紧不慢地跟在身后,像是看落荒而逃的小狗。
“再快点。”有人用鞋尖轻佻地拨弄她带着红痕的臀肉,惊慌间,刚被灌满的小穴微微抽搐,带着血丝的白浊顺着大腿根流下。“哎呦呦,这就淌水了。”一声怪叫引得众人哄笑。一个带着金链子的人,抽出皮带,“真他妈像条发情的母狗。”他不屑地抬手一挥,一记脆响,红痕烙在她的背部。
女孩痛苦地蜷缩在地上,几只皮鞋碾过她的身体、脸颊,勃起的阴茎在灯光下红得吓人。他们扯着她的发根,头皮被拽得生疼。紧闭的嘴唇几下就被龟头顶开,咸腥的前液糊满她的嘴唇。手上的麻绳终于被他们扯开,但不是心疼她,只是为了多几个可以侍奉的地方。
短短几分钟,她身上可以用的部位就被他们分好。有人坐在她的脸上,阴茎在没有牙的口中毫无顾忌地冲撞,冰凉的囊袋拍打着她的额头,杂乱的阴毛随着他的冲刺扎入鼻孔。刚刚失去童贞的下体,也被粗暴使用着。好在有残留的精液做缓冲,疼痛似乎减缓了一些。两只手、甚至脚,都被这些野兽拿来当做亵玩的工具。
但这些都不是让她最害怕的,当一个人看似好心地把她从冰凉的地上抱起时,还没感受到他胸膛的温热,那根烧红的铁棍就抵在她从未被碰过的后穴。女孩不顾口中还插着粗壮的阴茎,哀嚎着试图挣扎。但几秒就被身上的人制服。
“别动!”正在使用她嘴的男人,嘶吼着向下一压,刺耳的哭喊戛然而止。片刻后,干呕和呛咳让她的脸变成吓人的青紫色。“要怪就怪你那个烂赌的爹。”他调整着角度,狭窄的喉咙被一点点撕裂,太阳穴上凸起的青筋,在浓重的体味和毛发间,突突直跳。
当她喉部肌肉因窒息而剧烈痉挛时,他不满地攥紧她的发根,“放松!”在她本能地张嘴吸气时,他顺势一送,龟头楔入喉管深处。
“对!就是这样!”软肉缠在冠状沟上吮吸蠕动,他兴奋地低吼着,抱着她的头开始新一轮的冲刺。“贱婊子!这张烂嘴天生就是为了含屌的吧!操死你!”喉咙被摩擦得没了知觉,她因极度缺氧而双眼上翻,泪水混着唾液横流。
抱着她的男人,一边观赏这场近在咫尺的春宫图,一边将手指插入她从未被开垦过的后穴。她身体本能地缩紧,但两片臀肉被硬生生掰开。她试图反抗,但缺氧让她早已变成了案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当第三根手指强行突破括约肌时,她的腰猛地弹起又被正在使用她小穴的男人强行按下。“贱畜,想绞断谁?”突然的让男人倒吸了口凉气,他抓起面前跳动的乳肉,指甲陷进乳尖用力拧转,龟头突破层层阻隔,直捣花心口。
“你等一等!”举着阴茎想要插入后穴的男人,按住正在抽插小穴的同伴,“一起。”两人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一个死死钳制住女孩抖成筛子的臀部,另一个会意地往掌心啐了口唾沫,胡乱涂抹在紫红的龟头上。
“放松!”粗粝的指节强行撑开她紧涩的穴口,褶皱在指尖的压力中,忍不住收缩。湿滑黏腻的顶端抵在入口处,紧密的褶皱被一点点撵平、撑开。压抑的尖叫声从她堵着阴茎的嗓子中挤出,她瞪大眼睛,清晰感受着两根硕大的肉棍,一前一后在她不堪重负的身体中刮蹭、冲撞。
那层薄膜被凸起的青筋摩擦、蹂躏,在男人们粗重的喘息和淫笑中,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玩坏的玩偶,被死死钉住,一把把尖刀在体内做着活塞运动。冷汗划过身上新旧交错的指印、咬痕,手掌中不同大小的阴茎在飞速抽插着。白浊一股股射到她的脸上、口中和身体深处。她不清楚这场酷刑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眼前的景象开始摇晃、意识逐渐模糊……
另一边,浑身酒气的陈潜龙被手下扶着靠在沙发边。在男人去帮他倒温水时,他余光瞥过桌角放的那只透明塑料碗,深红色的液体和底部隐约可见的豆子,他猜测是红豆水。一抹轻笑从嘴角划过,听到脚步声传来,微睁的眼睛又及时闭住。
“龙哥……”他似乎醉得不省人事,男人轻声呼唤着,手在他面前晃了晃。但除了沉重的呼吸,没有任何反应。“水在这里,我先回去了。”惦记着那个被三哥玩完的女孩,男人见陈潜龙始终没有回应,放下水杯急匆匆走向门口。
“啪嗒。”门锁合拢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陈潜龙搭在沙发上的手指,不易察觉地动了一下。门外,脚步声远去,耳边被夏虫的嗡鸣声填满。他又静静躺了几十秒,确定房间里没人后,缓缓睁开泛着红血丝的眼睛。没有碰那杯近在咫尺的水,他伸长胳膊拿起桌角的塑料盒,放在月光下,细细端详。
盒子最上方有【谢谢龙哥】的纸条,他勾了勾嘴角,指尖拂过歪歪扭扭的字母,眼前闪过舞台上那张委屈巴巴的脸。打开盒盖闻了闻,浓郁的红豆香味,让他灌满酒精的肠胃一阵抽动。不过犹豫再三,他还是连盒带水一齐扔进垃圾桶,却将那张纸条仔细迭好,放进钱包的夹层中。
身上的酒气和香水味熏得他直犯恶心,陈潜龙喝了一大杯清水后,快步走向浴室。水流洗去了他身上的疲惫,也让他暂时放下刚刚房间里那个可怜的女孩。这样的场景,这些年他见过太多。没办法阻止,就只能逃避。
毛巾在短发上随意擦了几下,他换上干净的白色T恤,拿起门口鞋柜上的头盔和车钥匙,走向停车场那辆摩托车。这是他唯一的放松方式。他戴好头盔,在发动机震耳的轰鸣声中,驶离这片充满罪恶的富人区。
湿热的风掀起他的衣摆,摩托车在山间小路极速穿行着。他熟练地避开树叉和石块,十几分钟后,车停在一处悬崖边。
远处,万家灯火照亮夜空。陈潜龙从裤兜掏出烟盒,半倚着摩托车,目光停留在不远处的几个小土包上。土色还带着新翻的湿润,那些满脸惊恐、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的“残次品”快速在眼前闪过。
她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
他咬着烟嘴,深吸一口,暗红的火光照亮了他眼底的无力。“下辈子投胎时候,擦亮眼睛。”长长一声叹气后,他把未燃尽的香烟插在最近的小土包前。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