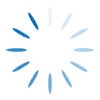崔授大费周章限制权贵举荐官员入仕,有公心,更有私心。
公心如何,无需多言。
私心则因权欲炽热作祟。
将天下选才用人之权悉数收归朝廷,自然也算收束到了他手中。
崔授清楚皇帝不希望世家势大,多用寒士于皇权而言是好事,皇帝定会半推半就默许此事。
那日书房偷欢过后,崔谨私下用了好几副避子汤药,依旧愁眉不展。
小桑一切如常,除了和小寻一起照顾她,就是侍弄花草。
崔谨犹豫再叁,支开小寻,单独试探小桑:“爹爹来的那日,你在书房外唤我,所为何事?”
小桑一听立刻红了眼眶,拿着小花锄抽噎,“向渡之前让我绣个荷包给他,我没绣,那回他来向我讨,我......我没有,他就抢走了我随身的一条手帕。”
“......”原来如此,崔谨将自己的手帕给小桑擦眼泪,问道:“他有没有欺负你?”
“已经欺负了呀,可小寻说这不叫欺负,他是喜欢我。都抢我东西了,怎么不算欺负?”小桑答非所问,红着眼气呼呼道。
“你说得对,不顾你的意愿感受,就是欺负。”崔谨捏着小桑沾有花泥的手哄她,并问道:“你对他可有意?”
“什......什么?”小桑呆住,一阵愣神。
这丫头年纪小,颇有些不开窍,崔谨索性将话说得直白,“你可心悦他?若让你们结为夫妻,你愿意么?”
“别别呀!小姐,别不要我呜呜呜......我就想跟在你身边。”小桑抱着崔谨的腿大哭,脏兮兮的小脸儿上沾的花泥蹭到了崔谨裙摆。
崔谨无奈扶起她,“你既无心,我会让他日后别再纠缠。那日你在书房外,可曾听到什么?”
小桑有些迷糊地回想了半天,“就隐约听到老爷声音很哑,他说......”
崔谨心跳漏了半拍,衣裙下的双手紧紧绞在一起,涩声追问:“说什么?”
“唔......好像是‘谨宝,乖孩子,爹爹爱谨宝。’”
小桑复述出来都觉得老爷太肉麻了,那么凶那么可怕的人竟然也会说这种话,不过他一向疼爱小姐,好像没什么稀奇。
崔谨紧绷的心弦微松,暗暗长吁一口气,“还有吗?”
“没了。”小桑摇头,“向渡拦着不让我靠近书房,就听到这一句。”
崔谨放下心,也没什么可嘱咐小桑的,太过明显的叮嘱,反而欲盖弥彰。
初雪过后,梅花渐开。
元清于府中设宴,邀请叁五名好友前来赏梅赏雪。
杨清竟也在其中。
这般文人最是恃才傲物、眼光挑剔,崔谨不知元清如何得了他青眼。
因婚礼时那段隐晦目光,崔谨待杨清格外客气有分寸,二人虽是旧相识,也只寒暄一两句,便想各自散开。
“你好吗?”杨清眼神温润,声音清朗,看着崔谨的眼睛,轻声问她。
他恰好站在一株梅树旁,素衣白雪,风骨卓然。
崔谨轻轻颔首,“有劳又渠先生挂念,我很好。”
杨清静待良久,没等到她的下一句,眼睛暗淡,“怎么不问问我好不好?”
“先生才名盖世,又于张节度麾下大展襟抱,想来自是春风得意。”
“......明怀。”杨清胸口起伏,最后一声叹息没入风雪,只吐出崔谨的字。
他从袖中取出一迭精心准备的纸笺,“塞外风景与京师迥异,可惜我拙于图画,无法画下来给你看,只能将其写做诗文。”
一纸文稿,除了塞外风雪,还有两人都心知的情意。
崔谨袖手而立,没有接杨清手中的诗文,她面容恬静,“又渠先生的文章传扬天下,坊间书肆多有刊印,何劳特意相赠?”
“......”
她不接,杨清死死捏着书纸,攥得指节泛白,眼眶隐隐发红。
他深吸一口气,不让自己在她面前失态,将诗文重新揣入袖中,笑意温柔儒雅,带着落寞。
“过两日我又要动身离京,下次见面,不知何时。”杨清受命为元秉做副使,一同往西境巡边。
“若你厌倦了此间纷扰,欲往山海寻仙问道,我......辞官归隐。”
杨清了解崔谨,知道她恬淡自适,一直有颗向道之心。
崔谨颇为动容,她心知杨清求官不易,满腹学识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如今却要轻易抛却?
只不过,即便要游历天下,崔谨心中也别有人选。
那个人,不是杨清。
“又渠先生!请慎言,还望自重。”崔谨面若冰雪,转身离去。
杨清望着她的背影苦笑不迭,连虚无缥缈的奢念也不肯与他么。
他脚下的梅瓣被踩碎,白雪红泥,同在一方天地,却恰如两个世界。
崔谨靠近与宴众人,就看到小桑这丫头同一人蹲在地上摆弄花草,叽叽喳喳说着什么。
“你上回帮我移栽的兰花长得很好,你想去看看吗?”
“嗯......还是不了吧,长得好就行。”小桑年纪小,平时十分娇憨,却很懂事。
崔谨走近,那青年公子急忙站起,正是元清的伴读沉镜。
沉镜容貌俊秀,鼻尖冻得发红,眉宇间尽是少年意气。
崔谨看他一眼,推脱身有不适,带着小桑小寻离席而去。
默认冷灰
24号文字
方正启体
- 加入书架 |
- 求书报错 |
- 作品目录 |
- 返回封面